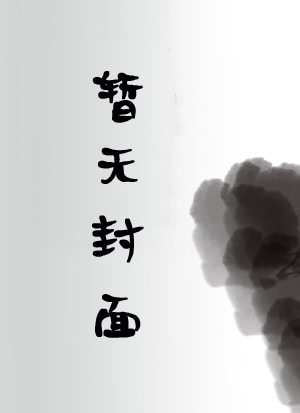翌日一早,霍厭就陪著孟晚溪去私人醫院做了詳細的產檢,去之前孟晚溪忐忑不安。
好在一切如常,孩子發育得十分健康,讓孟晚溪也鬆了一口氣。
她和霍厭去了一趟墓地,想要將這件事告訴給外婆。
為此,孟晚溪特地帶了結婚證,還有外婆生前喜歡吃的甜點。
山路難行,霍厭小心翼翼扶著她,「慢點,別摔了。」
「好。」
山風雖冷,有霍厭在身邊,孟晚溪一點都不冷。
到了外婆的墓地前,還沒有走進,她就看到了墓碑前擺放著兩籃鈴蘭。
她的腳步逐漸加快。
霍厭也看到了,開口詢問道:「外婆還有認識的人知道她過世嗎?」
孟晚溪的臉色大變,她死死攥著霍厭的手腕,她的力道一點點收緊,將霍厭的手腕都給攥紅了。
「晚晚?」
孟晚溪這才後知後覺回過神看向他,「外婆的老鄰居死的死,走的走,在郊外周圍也沒有鄰居,她的家人大多都在戰爭中去世,她的親人隻有外公一人,而外公走得早。」
「那這花……」
孟晚溪心中一痛,嘴唇翕動道:「是她,她回來了。」
霍厭很快就意識到她口中的這個人,「是你母親,對嗎?」
在港市的時候霍厭曾經問過孟晚溪,以霍家的能力,知道她母親的名字,要查到在哪裡並不難。
畢竟兩人訂婚宴這樣大的事,他想要徵求孟晚溪的意見,要不要將她媽媽找到。
孟晚溪對此十分排斥,在她心裡,那個母親早就死掉了。
可是今天她卻在這裡發現了鈴蘭。
外婆一生親人極少,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她喜歡的是鈴蘭花。
哪怕是傅謹修來祭拜,選擇的也是菊花一類。
孟晚溪就能確定,送鈴蘭的人,就是那個不要她的母親。
她本以為那個女人此生都不再會打交道。
畢竟當年的她那麼小,抱著孟柏雪的腿苦苦哀求媽媽不要走,她聽話的時候,女人沒有一點愛憐,一腳將她踢開,她的頭撞到尖銳的花壇,昏死了過去。
孟柏雪捲款而走,從此再也沒有回來。
別說那個年代的一千萬,哪怕是放在現在,一千萬也足夠普通家庭翻身,過上紅紅火火的好日子。
孟晚溪靠著外婆一天打幾分工養大,沒有任何保障,哪怕颳風下雨,外婆生病也必須要幹活。
有一次外婆差點病死也捨不得去醫院,是傅謹修背著她,走了許久才到了醫院。
孟晚溪拿著家裡所有的錢給外婆交了住院費,但也不夠她做手術的。
孟晚溪沒有辦法,去警局想要查找自己生母的下落。
外婆的腎上長了一個良性的腫瘤,切除就可以,隻不過檢查費用和手術費,以及術後的療養,前前後後加起來要兩、三萬。
對她們這個搖搖欲墜的家庭來說就是天大的數字。
外婆每天打零工掙的錢得給她湊一年的學費,雜費,生活費,以及家裡的開支,哪有那麼多存款去做手術。
孟晚溪隻想找到生母,從她手裡拿到三萬塊。
警方得知也很同情她家裡的情況,盡心儘力替她查。
查到的結果是在孟柏雪拿走所有錢的第二年,她就出國移民。
自此,毫無音訊。
有時候孟晚溪也懷疑過自己是不是她的女兒,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樣殘忍的母親呢?
將她帶回來,卻一天都沒過好日子。
孟晚溪要求也不高,她隻希望媽媽能看看她,對她多笑一笑,抱抱她。
可是那個女人每天不是醉生夢死,就是發酒瘋打她,用世上最惡毒的話罵她。
如果沒有外婆,孟晚溪早就死在了她的酒瓶子下。
那個早就消失在她記憶中的女人,哪怕是外婆的葬禮,她也沒想過告訴對方。
孟晚溪阻止霍厭去查。
不管孟柏雪過得好不好,都和她沒有關係了。
可是在一切都已經過去,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時候,她回來了。
孟晚溪看到鈴蘭就會想到當年的事。
她捂著頭蹲下,離別那天的畫面再度襲來。
「媽媽,不要走!」
「媽媽,不要丟下我好不好?我不能沒有你。」
「小賤種,就在這自生自滅吧,一輩子忍受貧窮的滋味。」
外婆上前拉住她,「你要走可以,錢不能全部帶走,這是丫頭掙來的,你得給她留下一部分將來讀書嫁人。」
「一個窮小鬼還想嫁人?她就適合去夜店賣。」
「啪!」
外婆狠狠給了她一巴掌,「你嘴裡不要不乾不淨的。」
孟柏雪憤憤不平,「媽,我可是給了你機會的,要麼跟我一起走去享福,你要管這個臭丫頭,就一輩子跟她耗在這。」
「孟柏雪,你不要她我要她,錢你一分都別想拿走,我現在就去報警。」
「媽媽,別走……」
「小賤種,去死吧。」
「丫頭!」
孟晚溪捂著頭,眼淚大顆大顆砸落在鈴蘭上。
想起來了,當天所有的事情她都想起來了。
那時候孟柏雪拿了錢是要帶外婆一起走的,唯獨要將她丟棄在那,外婆放棄了跟她出國的機會,一直守著她這個拖油瓶。
「外婆……」
孟晚溪淚水止不住,「你真的好傻啊。」
霍厭忙將她擁入懷中,「晚晚,怎麼了?別哭。」
「阿厭,當年我的頭被撞,導緻失去記憶也忘了你,但我現在都想起來了,外婆沒有和她一起離開,她選擇在那裡照顧我長大。」
霍厭一邊給她擦著眼淚,一邊問道:「這麼說,你母親原本是打算帶走外婆的。」
「是的。」
「很奇怪不是嗎?即便她沒有良心要離開二嫁,血濃於水,再怎麼恨孩子父親也會安頓好你,一千萬哪怕她拿出十萬也都足夠了,她為什麼對你這麼大的敵意?」
孟晚溪搖搖頭,「那時候我太小,她幾乎大多時候都被酒精麻醉,沒人知道我的父親是誰,我是跟我外公姓孟的。」
霍厭越聽越不對勁,「從你的描述,我感覺不到任何的母愛,她倒是和詹芝蘭如出一轍,晚晚,有沒有一個可能,你根本就不是她的女兒?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