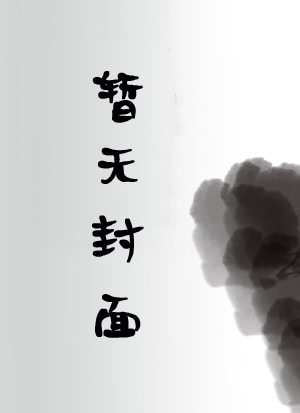宮中之前提交出來的口供,宇文皓為了謹慎起見,讓顧司找當時在禦花園裡頭的宮人再問一遍,看看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。
顧司也不放心伏素的人辦事,親自帶着禁軍去問了一遍,又去了一趟貴妃宮中,問阿彩與汝側妃。
汝側妃的說辭是滴水不漏的,雖然看似很不符合她做事的方式,但是挑不出錯處來,為了給王爺解圍,請了當時在素心殿裡頭看着扈妃摔倒的安王妃出去,然後安王妃腹痛,無法走道,安置在就近的上弦月亭裡頭,怕風大而落了簾子,都沒有任何問題。
至于阿彩之前的口供是乏善可陳的,連唯一着重點是她跑到上弦月亭裡去的,可當時已經有人發現安王妃遇襲了,簾子已經掀開,就是說,她在安王妃被汝側妃帶走到遇襲,她都沒有在身邊,更不是頭一個發現。
她本是安王妃貼身侍女,可在這件事情上頭,她完全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的信息,唯獨一點有用的是她說安王妃當時穿的裙子不是紅色的。
換言之,鎮北侯看到那一抹紅色的裙裾,未必是裙裾,而是血迹。
可這隻是鎮北侯的一面之詞,或許遞上刑部或者大理寺的時候,不足以采信,甚至還會說他故意引導主審調查的方向,讓主審以為他在接近上弦月亭的時候,安王妃就已經受傷,用以撇清自己的嫌疑。
問完了兩人,安王負手而出,顧司看到安王的時候吓了一跳,不過是短短一天,但是安王卻憔悴了許多,眼睛通紅且眼窩深陷進去,眸光如同鋒利的刀片,叫人乍一眼看過去,十分冷冽瘆人。
“顧司!”安王陰鸷地眸子揚起,盯着顧司,“你去告訴宇文皓一聲,休想為那老匹夫開脫,本王也問過,當時禦花園裡多半是世家哥兒小姐,要麼就是宮中奴婢與太監,且當時在場的人,除他鎮北侯之外無一人懂得武功,就這一點,他怎麼洗都洗不脫罪名,本王會盯死他,他若不死,本王不惜犯下殺人重罪,也不會饒恕了他。”
顧司發現自己竟然有些體諒安王,或許是因為他也成了親,有深愛的夫人,安王寵妻人所皆知,如今安王妃生死未蔔,他唯一的執念就是殺了兇手,因此,顧司并未說太多,隻道:“王爺放心,此案關系重大,兇手絕對不能逍遙法外的。”
安王厲聲道:“兇手就是鎮北侯那老匹夫。”
顧司本不想辯駁,但是,聽了這話覺得有些刺耳,道:“王爺的心情,微臣很理解,但是,如今真相如何未曾查明,王爺這般武斷,鎮北侯是兇手還好說,若不是,豈不是叫兇手逍遙法外嗎?”
阿汝在旁邊插了一句話,略帶悲憤的語氣,“顧大人這話有偏頗之嫌,方才王爺說了,禦花園裡,就唯他鎮北侯一人懂得武功,王妃是被掌力所傷的,這說明兇手除他之外不做第二人想,我知道太子與鎮北侯如今的關系不錯,可不能因此徇私,顧大人,王妃還躺在裡頭生死不知,連腹中孩兒都沒能保住,你們辦案,要講良心啊。”
阿彩也哭了,“是啊,務必要将兇手伏法,太可恨了,王妃手無縛雞之力,心底更是溫柔善良,多兇悍的人才做得出這般惡行啊?若不把兇手伏法,王妃府中的世子豈不是白白犧牲了?”
顧司見安王聽了阿汝和阿彩這句話之後,眸子一下子就竄起了狂怒,逼前一步,額頭青筋跳動着,盯住顧司,冷狠地道:“你聽着,三天之内,若京兆府還拖拖拉拉不肯結案,本王就親自去了結兇手。”
顧司不願去挑戰安王的底線,隻得應了一聲告辭。
他歎氣,安王這邊執拗地認為鎮北侯是兇手,如果三天之後調查不出來結果,隻怕他真會去殺了鎮北侯。
一個憤怒的人,什麼事做不出來?
顧司随即又去問了一下當日在禦花園的宮人,還去問了一下發現安王府出事的人。
發現安王妃的是和郡王府家的世子妃,所以顧司派人去告知宇文皓,叫宇文皓到和郡王府去取供,他則繼續留在宮裡頭問。
宇文皓去了一趟和郡王府,世子妃昨晚回來就吓得病了,聽得說太子來問昨天的事情,由世子扶着出來。
見禮之後,世子就扶着世子妃坐下來,宇文皓見世子妃的臉色青白一片,嘴唇都是烏紫的,眼底也黑了一圈,滿眼的驚惶,可見着實是吓得不輕。
世子妃道:“昨天妾身帶着侍女在禦花園裡頭走了一圈,本是想着去賞梅的,殊不知梅花開得不多,路上遇到幾位夫人,寒暄了一會兒,便覺得乏了,想尋個地方歇一會兒,喝口熱茶暖暖身子,因與上弦月亭比較近,加上看見下了簾子,想着裡頭應該也有人,便正好說說話湊湊趣,等晚宴舉行的時候再回去,殊不知……”
她說到這裡的時候,猛地打了個突,忙喝了一口熱茶鎮定下來才繼續說下去,“殊不知剛上了石階,我家侍女便說怎地聞到一股子血腥的味道,她說的時候我便馬上福身問裡頭是哪位夫人,問了兩聲聽不到答應,侍女便掀開了簾子看了一眼,便見有一人坐着身子前傾趴在石桌上,底下流了一灘的血,我吓得不行,忙叫侍女進去看看,侍女去叫了兩聲,伸手去輕輕地推了推,便見那人倒地,躺在了血泊之中,我當時還未曾看清楚是安王妃,隻吓得尖叫起來,後便有人陸續跑過來說是安王妃,且安王妃小産了,之後我被人扶走,便不知道後面的事情了。”
宇文皓聽完之後,叫了侍女出來問,侍女說的話與世子妃沒有什麼出入,基本就是這樣。
世子妃撫着胸口難過地道:“當時驚慌之中,大家都以為安王妃隻是小産導緻昏倒的,竟不知道是遭了毒手,實在是太殘忍了,安王妃這麼好的人,且懷着身孕,竟然要遭此橫禍,太殘忍了。”
世子安撫了她一下,轉頭問宇文皓,“太子哥哥,聽說兇手是扈妃的父親鎮北侯,是不是?”
宇文皓看着他道:“案子還在調查,誰是兇手未知,不可草率下定論,你也不能對外胡亂揣測,知道嗎?”
世子點頭,“臣弟知道,臣弟是不敢在外頭說半句的,隻是今日我出去了一下,聽得大家都在議論紛紛,說鎮北侯就是兇手。”
宇文皓深感無力,回頭又有輿論出來作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