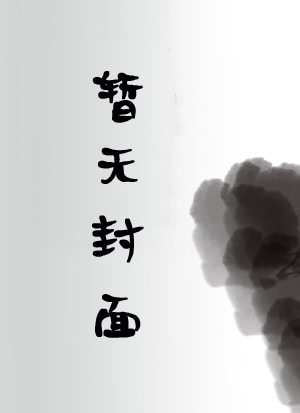齊王的臉有好幾道疤痕似的東西,一紅一青的,布滿了整張臉。
宇文皓問道:“你臉被藤條打了?”
齊王臉色有些不好看,小聲嘀咕道:“關你什麼事?别問。”
袁詠意欣然解釋,“是打的,帶他去了一趟護國寺求見主持,主持說他鬼魅纏身,為他驅趕邪祟,用幹柳枝打的。”
“好端端的,為什麼去護國寺問這些?”宇文皓問道。
袁詠意瞧了齊王一眼,想起他的病不能說,遂笑笑,“不如意便去問問。”
齊王怕她亂說,便起身拉着宇文皓出去說話。
袁詠意開心地問元卿淩,“我聽說元姐姐肚子裡懷的是三個,真好。”
元卿淩笑着看她,“齊王的病好些了嗎?”
袁詠意搖頭,“不知道,他也不叫人看,我回去找祖母說了這件事情,祖母說如果醫治沒有希望了的話,就去護國寺找方丈驅邪,這不,就帶他去了嗎?”
“方丈說沒事?”
“不是沒事,是說邪祟纏身。”
元卿淩笑了起來,那就是沒事。
好歹也是做科研的,竟然學神棍驅鬼,有本事。
隻是,齊王沒事裝病做什麼?還騙得袁詠意那麼關心他。
兩人在屋中裡說了會兒話,便聽得蠻兒進來說,紀王妃叫人請王妃過府。
元卿淩怔了怔,“叫我過去?”
“是的,”蠻兒招呼紀王妃身邊丫頭佩兒進來,“是佩兒來請。”
佩兒進來行禮,“楚王妃,我家王妃請您務必到紀王府去一趟,府中出了要緊的事。”
“出什麼事了?”元卿淩問道。
和紀王妃雖算不得太熟,之前嫌隙也還沒完全解除,卻也知道她這人,若不是真發生了重大的事情,不會貿貿然請她去。
佩兒上前道:“王妃隻說請您務必去一趟,有些事情,需要您親自處理。”
“我去處理紀王府的事情?”元卿淩愕然。
“到底什麼事啊?”袁詠意問道,見她支支吾吾地,便沉下臉,“說!”
佩兒這才再上前一步,輕聲道:“褚妃娘娘發現王妃佛堂裡頭藏了一個小人,那小人身上紮滿了針,寫着的是楚王妃您的名字和八字,如今已經驚動了紀王,紀王說要把紀王妃扭送到宮裡頭治罪。”
袁詠意大怒,“這是厭勝之術,誰這麼膽大不要命了啊?這是詛咒!”
外頭的喜嬷嬷聽得此言,也急忙進來了,怒容滿臉,“是紀王妃做的?她原先送來的那個觀音就是詛咒,如今我們王妃有恩于她,她恩将仇報嗎?”
佩兒吓得都跪下來了,哭着道:“不會,王妃不會再這麼做了。”
袁詠意橫眉豎眼,厲聲道:“不會這麼做?那為什麼從她的佛堂裡頭搜出來的?如今紀王要扭送她入宮去,她便想着元姐姐心地善良,叫你來請元姐姐過去好為她求情,說原諒她是不是好免罪是不是?休想,她這般惡毒心腸,就該扭送進宮治罪。”
佩兒哭着辯解,“不是,真的不是,袁妃娘娘,王妃是冤枉的。”
“請王爺!”袁詠意下令道。
蠻兒即刻便去找宇文皓。
宇文皓聽了這事,和齊王急匆匆地趕了出來。
宇文皓臉都黑了。
之前他因為被杖打,湯陽便去找了個師父問問,說楚王府最近确實是招黑,叫注意一點,所以他心裡頭就很忌諱這些事情。
如今聽得都小人紮針了,這等惡毒的厭勝之術,還是沖着懷孕的老元來,他怎忍得住這口氣。
不過,他倒沒有理智全然喪失,隻冷冷地道:“既然來請,我們就過去一趟,那小人不管是誰做的,今日都要揪出來不可。”
元卿淩倒是相信紀王妃的。
倒不是說紀王妃人有多好,或者是現在病着要找她治療。
而是紀王妃如果真的在佛堂裡頭藏了這麼個犯忌諱的東西,褚二是絕對不可能進去搜到的。
這是一個局。
這個局,讓紀王妃這麼毫無防備地就套進來了,隻怕不是褚二一個人的手筆。
那口口聲聲說要扭送紀王妃入宮的紀王,是否也摻和其中呢?
如果是,他為了扶褚明陽上位,可真是費煞苦心了啊。
齊王夫婦也跟着他們一塊過去了,喜嬷嬷自然也跟着,她一路上火大得很。
到了紀王府,大門緊閉,可見佩兒是偷偷地跑出去通知元卿淩的。
宇文皓敲開了門,直接就闖了進去。
人都在正廳裡頭,紀王怒容滿臉地坐在正座之上,見宇文皓和元卿淩來了,他神色微微一怔,冷冷地掃了一眼安靜地坐在旁邊的紀王妃一眼,便随即站起來,歎了口氣,道:“老五,大哥對不住你,你大嫂做下了此等惡毒的事情,你放心,大哥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,不會輕饒了這毒婦。”
宇文皓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個小人。
小人是用布做成的,一襲的白色衣裳,這衣裳很眼熟,更眼熟的還有臉型發飾,活脫脫就是一個小人版的元卿淩。
那小人渾身都紮着刺亮的銀針,背後釘着一塊布料做成的東西,寫了元卿淩的名字和生辰八字。
而最讓他糟心狂怒的是這小人也是孕婦,那肚子上赫然紮着好幾根針,且都是沒入了小人裡頭,隻留下針頭。
宇文皓滿臉鐵青,看着紀王,咬牙切齒地問道:“是大嫂做的?”
紀王怒道:“就是這個毒婦做的。”
宇文皓慢慢地轉過頭去看着紀王妃,紀王妃身穿一襲青色棉襖,手靜靜地放在扶手上,臉色有些蒼白,整個人有些可憐。
她看着宇文皓,然後再看着元卿淩,最後,落在了褚明陽的臉上,緩緩搖頭,“不是我做的。”
褚明陽頓時站起來,冷笑一聲,“喲?剛才三番四次問你,是不是你做的,你一句話都不說,隻默認了,如今冤有頭債有主,你不承認了?”
褚明陽今天穿一襲绯紅色的緞裙,披着白色狐裘披風,手中捧着一個暖手小爐,說不出的雍容與貴氣,若不說,還以為她才是紀王正妃。
反觀紀王妃,真的是寒酸與落魄。
不過,紀王妃的頭慢慢地擡起來,唇瓣輕輕地一勾,“因為,沒有我的人在,我否認也無用,你說得對,冤有頭,債有主,如今他們都在了,那這事就好說。”
一下子變得淡定的紀王妃,不再是元卿淩他們進來時候所見的那麼弱不禁風不,堪一擊。